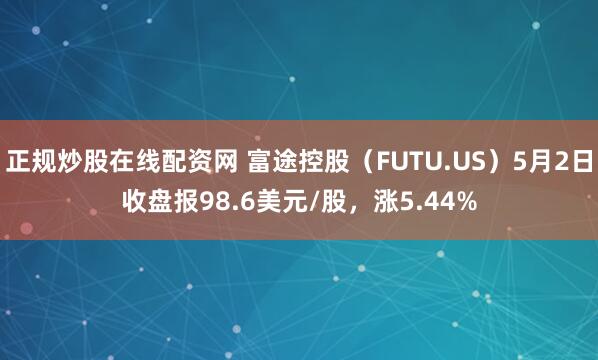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配资网首页官网,“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融合已成为全球性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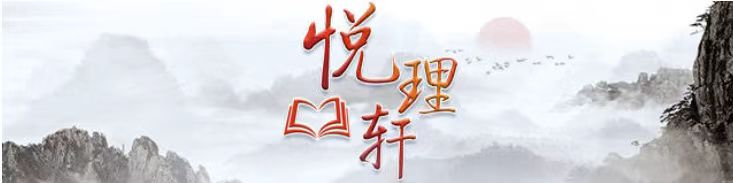 文|悦理轩
文|悦理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融合已成为全球性趋势。
当前,全国各地正加快推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着力强化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应用。数字技术为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伴生着新的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构成了推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面对的基本矛盾。
因此,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既要遵循对立统一规律,深刻认识并统筹把握机遇与挑战;也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统一,在全面兼顾中抓住关键环节;更要正确处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立足各地实际,探索科学精准、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实践路径。
一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统一的原理要求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一分为二看问题,既要增强机遇意识,又要强化风险意识。同时要善于吸取有利因素,通过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双向融合,化风险为机遇,推动数字生态文明向更高水平迈进。
首先,数字技术通过创新治理技术增强生态环境治理的科学性。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和云平台等技术构建的“空天地一体化”生态系统监测体系,能够实现对土壤、水质和植被等广泛要素实时监测。数字技术通过拓展生态环境治理对象的空间广泛性和时间连续性,帮助收集更多有效生态数据,有助于更全面反映生态系统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广泛性和前瞻性。
其次,数字技术并非天然具备绿色属性,其应用潜藏多重生态挑战:数字基础设施依赖能源和材料密集型产业,面临废弃污染风险;数据中心需大量能源供电,而当前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加剧了能耗与碳排放压力;其庞杂设施占用大量土地,服务器降温又消耗巨量水资源,进一步挤压区域生态系统。可见,若缺乏绿色发展理念引导和制度规范,数字技术可能催生新的环境问题。
最后,面对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应坚持“软硬兼施”策略,寻求绿色化转型路径。一方面,各地应因地制宜制定数字基础设施绿色发展“软标准”,明确对数字基础设施的绿色发展标准。另一方面,要加快绿色数字“硬技术”的研发应用。推进低碳云计算等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绿色能源利用率,减少数字基础设施碳足迹。
唯有统筹好数字化和绿色化,才能在变革中保持治理的有序性与可持续性,推动数字生态文明走向高质量发展。
二
事物内部的矛盾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既要统筹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又要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带动全局。当前,建设数字生态文明仍处于探索阶段,这要求需在把握整体逻辑的基础上抓住关键要素,实现系统性提升。
首先,数字生态文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多重矛盾关系:一是赋能增效与资源消耗的矛盾,数字技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环境治理,但其基础设施制造、运行、报废过程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二是信息透明与数据鸿沟的矛盾,数字技术促进环境信息公开透明,但可能加剧不同地区、群体的“数字鸿沟”,并带来数据滥用、隐私泄露的风险;三是虚拟感知与现实行动的矛盾,大的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需要转化为有效的线下治理、修复和保护行动;四是技术逻辑与生态逻辑的矛盾,技术的标准化、效率优先逻辑可能与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复杂性、非线性逻辑存在张力。
针对这些矛盾,需以统筹兼顾的方法把握整体运行逻辑:推动“绿色数字技术”发展(如低功耗芯片、可再生能源供电的数据中心等);弥合数字鸿沟,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并普及基础设施;建立数据安全与开放共享的平衡机制;促进虚实融合,协调技术逻辑与生态伦理。
其次,深化数字技术的生态应用是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突破口。数字生态文明本质上是治理主体合理运用数字技术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主要表现为:
应以生态环境治理需求为导向,聚焦关键难点,提升数字技术适配性;应构建技术应用长效机制,完善统一的标准规范、评价及运营机制,避免“建成即落后、上线即淘汰”的“次抛”浪费;应树立正确政绩观,重实效而非数量,提升理论转换能力,做到既能理解数字生态文明的理论内涵,又能精准把握实践需求。
最后,要通过对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和重点主体的系统突破,带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由局部探索向全面深化推进。
在重点领域,应聚焦数字化绿色制造、智慧能源系统深度转型等场景;在重点区域,应选定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两山”理念实践创新基地等,打造“绿色智慧”标杆工程,同时系统总结经验、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形成可复制推广的“解决方案集”;在重点主体方面,应推动龙头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先行先试,建设数字生态技术平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增强全国一盘棋意识,加强政策措施的衔接协调,确保形成合力;又要充分考虑区域资源分布和产业分工的客观现实。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推进全国范围内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部署,也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发挥各地优势。
首先,绿色化和智慧化是构成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普遍性要求。绿色化强调的是生态环境友好型的技术与制度架构,要求在技术开发、设施建设、能源利用等各环节贯彻节能减排的生态化原则,避免数字基础设施成为生态负担。智慧化则体现为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数字技术,实现环境监测的实时化、生态决策的科学化和治理手段的精准化。
由此可见,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普遍性目标,推动绿色化和智慧化融合发展则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
其次,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在生态资源禀赋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方面呈现出不平衡的特征,这就决定了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不能“一刀切”,而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对于发达城市,其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技术储备成熟、资金与人才资源充足,可优先布局绿色建筑和智能交通等系统研发,构建生态友好型城市运行新模式。对于资源型地区,因长期依赖煤炭和矿产等资源密集型产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较为突出,应重点发展以生态修复为目标导向的数字治理体系。对于欠发达地区,发展基础相对薄弱,但生态空间广阔。因此,应依托本土自然资源优势,通过生态资源数据化、数据资产化、资产服务化的方式,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总之,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不是简单的“数字技术+生态环境”叠加,而是在尊重物质世界客观规律基础上,运用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深刻分析并有效化解系统内外各种矛盾,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治理创新的协同融合,推动人与自然关系在数字化时代实现更高水平和谐共生的辩证实践过程。
【执笔】蓝强 罗颖妍(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栏目责编】李育蒙
【频道来源】南方+客户端观点频道
鼎宏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